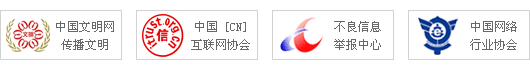她是对的,我对做饭这事毫无感觉。最重要的是,只有当你对烹饪程序了如指掌时,菜谱才有用。剥洋葱、烤碎牛肉、加上酒并将酒精燃烧掉、撒点盐——制作一道最基本的番茄牛肉酱所必备的全套流程——一旦你知道要怎么做,一切都会很简单。不过,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那母亲写下整整两页纸的菜谱就合情合理了。
番茄肉酱的制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足以让人感觉烦躁。用这话来形容母亲对待烹饪的态度可谓恰如其分,尽管在吃的方面不是如此。在那些年里,对食物的爱恨交加是很平常的,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说的:作为一名食客,母亲和食物的关系相当直截了当。她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去享用它,尽管她抱怨食物让自己增磅,但吃喝能给她带来简单切实的快乐。然而,烹饪却不一样。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尽管这是母亲的拿手好戏,但我却不能肯定她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这其中干系重大。
烹饪技能是我的母亲茱莉亚·冈尼甘在一种不寻常的境遇中迟迟学来的。1920年她出生于爱尔兰西部一个穷困小村庄里。母亲是长女,连她在内,八个孩子中有七个是女孩。她选择了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最为迷人、最不可思议的道路:成为一名修女。她修行于一个名为“进殿派修女联合会”的传道组织。授予圣职后,她更名为修女鄂奇丽亚,其后十五年光景大多在马德拉斯(即现在的金奈)度过。那里有进殿修女会的几个分支教会学校,合称“教会公园”,母亲晋升成为师范学院校长。1958年,母亲的忽然辞职在马德拉斯的教育界轰动一时,对于她本人而言,这样的转变更是天翻地覆。脱下修女服,毫无财产,离开马德拉斯,只身飞往伦敦——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方,而全身的现金只有10英镑。
母亲所看到的外部世界,跟梵蒂冈宗教气息浓厚的封闭世界比起来,一定有着天壤之别吧。她先是在伦敦遇到了我父亲,然后结婚生子,其间跟随身为银行经理的父亲几番升迁,从德国汉堡城到印度加尔各答,又从印尼婆罗洲到缅甸、香港。四十多岁时,为了跟上这个广阔的新世界,她被迫学会了许许多多技能,烹饪就是其中之一。简而言之,这就是为什么母亲对自己的厨艺如此担忧的原因。
她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农民的妻子、一个好厨子,在此,好厨子的意思是在基本没钱的情况下,还能喂饱一大家子的人。在三十年代跟“饥饿的四十年代”,爱尔兰乡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缺钱。在那种捉襟见肘的状态下,只有茶叶和糖要到商店购买,其他食物都出自田间。搜寻、储藏、应季而食,我这位住在梅奥郡的祖母总是站在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布鲁克林食物风尚的潮头。我母亲不是那类厨子,她不断将自己改造成为一名游刃有余的家庭主妇,一个可承办各种酒会、晚宴的发起人,知道许多五花八门的外国菜名,以及如何将它们调制出来。烹饪是她自我创造计划的一部分,使她成为了与往昔的自己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人。
我母亲开始对烹饪发生兴趣的具体细节不同寻常同。把学习做俄罗斯酸奶牛肉,当作在马德拉斯经营修道院学校的一种解压方式,她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不过与此同时,她的故事也很典型:人们开始用食物进行自我表达和定义。如果你像你祖母一般生活和烹饪,可能从不看食谱。食谱和它所象征的意义,正是为那些不遵循祖辈方式生活的人所准备的。
曾经,食物关乎你来自哪里,现在,对大部分的我们来说,食物关乎我们想去往何处、想成为怎样的人、选择怎样生活。食物一直是一种身份的表达,但是如今这些身份更为灵活多变;它们随着时间变化,对不同压力做出反应。甚至有些方面是荒谬的:泡菜热、越南面包潮、韭菜革命、必吃甘蓝。泰国北部仍是关注热点吗?动物下水已经扔掉了吗?哥本哈根食谱过时了吗?食物和时尚的交集是愚蠢的,就像时尚与其他任何事物的交集一样无聊。然而,在一些关键意义上,隐藏在食物之下的,是一种身份的表达,是有意识的选择。对于历史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真实的。食物时尚和趋势中显而易见的无知和肤浅所触及到的深层意义是:我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想成为什么人。
二十世纪末,似乎所有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在购物、做饭和外出就餐,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出现与自我定义、自我表达、创造身份、追赶潮流、大肆宣传和新新事物有关,有时不得不与新奇(泡沫!凝胶!胶化成球!)和新的变老方式(慢食!从农场到餐桌!乡村火腿!)相伴而生。我妈妈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已经花了大部分工作时间撰写有关食物的文章,人们经常会被我怎样和为何对它感兴趣。我从来给不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因为对于我,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模式才逐渐清晰起来。到现在为止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对食物的兴趣来自于伴随我成长的人,对于他们而言,食物的价值可与很多人当下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相媲美。

我意识到,当我们思考食物时,大部分注意力与食物无关,而是关乎焦虑。食物使我们焦虑。无限的选择范围和可能的自我表达意味着很多方法会出错。你可以使人生病,也可以让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人们觉得食物选择成为别人评判自己的依据,这种感觉是正确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我曾经两次担任美食评论家,1992年到1995年是在《伦敦观察》,2012年到2013年是在《卫报》,在这两段工作之间(我花了几年的时间为《英国绅士》 杂志撰写美食专栏),发生了很多巨大变化。首先是食物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遍地都是。这一趋势持续走高。我们在烹调和食用的食物都比过去好很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奇怪的是法国要另当别论,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第二大变化是我在餐饮界变得更有名气了,这大多要归功于我的第一本小说《快乐债》,出版于1996年,名列畅销书榜首,以及一位痴迷于美食的疯狂叙述者。这本书赢得了茱莉亚儿童食谱奖——如今,只要有人理解美食在自我创造方面的重要性,就可以以他/她的名义设立一个奖项。我在这个行业有些熟人,最珍贵的收藏之一是一张照片,那是在芬兰一次由我主讲的论坛上拍摄的——我坐在沙发上,旁边是韩裔美籍厨师大卫·张、世界知名的丹麦厨师勒内·雷哲皮、意大利顶级主厨马西莫·波图拉,以及知名作家马格努斯·尼尔森。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为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加以佐证。在美食世界,我不是忿忿不平的门外汉,不是那种一谈及美食就感觉像打着灯笼做爱的清教徒,但是,我确实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与食物相关的许多事情都走岔了路。
1995年我第一次放弃美食评论时,记得当时我的想法是,世人对美食的迷恋就像泡沫:我们已经达到了美食高原期。这也许是我错得最离谱的一次。当代人迷恋于食物、厨师、名厨、电视大厨、对原料、烹饪和进食,以及我们喂饱自己和我们的孩子的物质,还有到哪里吃、如何通过食物来定义自身——所有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与食物相关的网上产业甚至还未起步。
如果让我用两个词来概括随后二十年所走的弯路,那就是:太多。什么都太多了。太多炒作、太多页面空间、太多程序时间、太多特色、菜谱、旅行餐,以及回顾,概要和论证,太多太多在线评论、判断,还有唠叨。以我的经验,尽管厨师从风起云涌的眼球关注中受益最多,他们却大多保持谨慎。我经常开玩笑说,美国烹饪学院除了开设美食历史和厨房技能的课程外,还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教学模块,名为“假装不讨厌博主”。厨师们如同生活在接收终端,评论和批评络绎不绝,加之恶意的叫嚣和口碑点评,在他们眼中,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对他们的手艺知之甚少的人。
他们说,每个人都是评论家,在当今的食物世界,这句话确实没错。当然,每个人一直都是评论家,总是要由顾客们对一切做出最基本的判断:我想当回头客吗?但是就数量和音量的双重意义而言,当代人更注重量。所有喋喋不休的批评声音甚嚣尘上,比以往更难以忽视。谈论和了解食物是我的最大乐事,但是,这种在私人和个体层面上都说得通的爱好已在更广泛的文化中不成比例地生长起来。想象一下,假如你痴迷于火车模型,对此兴趣盎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念着,燃烧着你的热情。但接下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整个文化都变得对模型火车痴迷起来,有关模型火车的博客成倍增长,杂志封面上到处是火车模型制造商的广告,电视上转播着火车制造PK实况,而且享受着新一代摇滚明星的礼遇。对你而言,凡是与火车模型的一切或许依旧给你带来无上的乐趣,不过在内心深处,你可能认为它已经有点儿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了吧?那就是时至今日食物给我的感觉。
在那二十年间发生的另一项变化涉及到伦理学。不久前,食物只是食物。(我已记不清曾经跟业内人士交谈过多少次,在一些观点上争来争去,结果总会有人耸耸肩说“这不过是食物而已”。)如今可就不一样了,食物既能维持生命,同时还是关系到政治和伦理。购物时人们压力山大,食物要吃得负责任、吃得健康、吃得可持续。至少,这是与食物文化相关的文字和谈话留给公众的印象,是政治代言的一种形式。对一些人来说,它不仅为政治代言,还是真实交易,是迫在眉睫、关系重大的政治。爱丽丝·沃特斯对此阐述得很漂亮:“饮食是一种政治作秀,只不过与古希腊人使用‘政治’一词的方式如出一辙——不仅意味着与投票竞选有关,还意味着‘我们与他人的所有互动或与之相关的一切’——从家庭到学校,到社区、国家和世界。我们在每个层面对食物所作的每个选择都至关重要,正确的选择能拯救世界。”
或许这些观点在乌克兰、利比里亚或伊斯兰国组织所辖地区不能引起共鸣,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温暖感人、慷慨宽宏的精神——当我们购买夏玉米、纯种西红柿和户外放养的有机土鸡时,行动中已承载了政治意义。通过上述选择,我们正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种想法可以拯救地球,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每个层面上都至关重要”。
这种见解令人震颤,但我发现自己不能苟同。首先,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养活整个世界。如今,世界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这是一种良性发展,因为从环境角度来看,人口集中是件好事。同时据联合国消息,到本世纪末,世界总人口将达到约110亿。我们也许能应付得来,但是,没有工业化农业,一切都是空谈。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我们消费者选择的个体价值,但这确实意味着,在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进程中,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仅限于此。在我的生活中,如果购物和烹饪真的是最重要、最具政治意义的行为的话,或许那也正表明我们的政治观念大大缩水了——缩小到可以装入我们的环保购物袋。如果连消费者选择之类微不足道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都具有极大意义的话,我们也许就无法对足够大的空间进行思考和作为。想象你即将升入天堂时,站在由托马斯·杰斐逊、埃莉诺·罗斯福和马丁·路德·金组成的陪审团前,你的任务就是看着他们的眼睛来描述自己,你说:“我从里到外都是新鲜的、具有地域性和季节性。”
每天逛超市时,这些想法都会非常频繁地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新鲜、具有地域性和季节性。我并不认为我的选择会改变或拯救这个世界,但是这正是我喜欢烹饪和吃的原因。昨晚我烤了松鸡,在英格兰,这种超级古怪的野味只有在8月12日至10月10日间才有。今晚,我要做番茄肉酱,这是第几次做我早已数不过来了。过了这么些年,我见识到了各式各样肉酱的做法,有用加入鸡肝做成的常规的肉酱(我妻子很喜欢,因为过去岳母这样做),还有用三种肉——猪肉、小牛肉和培根以及三种调料——料酒,牛奶和番茄酱做成的肉酱。然而我现在经常回味的是母亲做的,方法最简单,却最好吃:做法是将洋葱、碎牛肉、番茄酱、罐装番茄、料酒、百里香、盐放在一起炖至少三小时。我的孩子们也喜欢,他们一直都好这口。烹饪让我想起母亲,总是如此。母亲并不认为烹饪改变了世界。但她深知,烹饪是自我救赎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我们很多人,它同样适用。对我而言,这种意义足够深远。